鲁迅对谈太宰治?这波梦幻联动让我狂喜
知乎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:假如鲁迅和太宰治三人坐出来,彼此聊聊天的话,会聊些哪些?
这个问题既玄乎,又逗趣。
玄乎的是,不了解两位诗人生平的,乍一见这话题,心里便会一喜:鲁迅和太宰治居然有交集?
这真是梦幻联动!
逗趣的是,只要稍对二人有所探究,便会发觉,鲁迅和太宰治的确并未认识过。
虽然,1909年——这一年,二十八岁的鲁迅离开东京回到中国,而太宰治才刚才出生。
二人的天差地别除了在时空国别之上,更在于截然的个性之间。
鲁迅,刚毅的战斗者、独行的猛兽、敢于直面低迷人生与淋漓血水的骑士、怼人大师、逢吵必赢的嘴炮MVP。
太宰治,丧文化祖师爷、文青界的icon、懦弱美学创始人、“人间不值得”的先行者、自杀专家、广大“自诊”抑郁症病人的精神知已。
鲁迅说:“希望附丽于存在,有存在便有希望,有希望便有光明。”
太宰治说:“我想死,必须死,活着只会成为罪恶之源。”
一个是阴郁如骄阳的自强者,一个是随时随地想着自尽的自戕者,非要说共同点,大约便只有——
“你若安好,便是阴天。”——鲁迅:这不是我说的。
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。”——太宰治:这也真不是我说的!
但是,在真实的历史中,自强不息的鲁迅,与自戕消沉的太宰治,却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交集的——虽身体从未得见,灵魂其实已经聊得畅快了。
鲁迅于1936年逝世,在此之前,太宰治已在台湾艺坛崭露头角。
鲁迅阅读他的作品,并这样评价他:
“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太宰治名言,卑贱而自由。
他想要打破哪些,却又没有方向。
他的痛楚在于他用心看着黑漆漆的世界。”
相比于鲁迅一贯精妙到势利的洞悉,太宰治对那位异国的艺坛高手,却要“狂热”许多。
他称鲁迅为“中国文学逸才”,得悉鲁迅曾喜爱过他的小说,他不禁“狼狈焦躁、面红耳赤”,简直就像中学生被批阅作业。
生命末尾,在《纪念鲁迅同志》一文中,太宰治更是这么坦言:“渐渐地,我开始怀念一个人,想得不得了,想见到他的脸,想听到他的声音,想得不得了,似乎是腿上扎着滚烫的推拿,只能忍让着不动一样。”
——知道的明白他在写鲁迅太宰治名言,不晓得的,还以为他在写情书。
他甚至还手抄过《朝花夕拾》,像粉丝抄偶像的歌词。
其实,最直接的“粉丝”行径,还是他在1945年——生命中止前的前两年,发表了以鲁迅为主角的传记体小说《惜别》。
这是世界文学中惟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,更是同一时代中,一个文豪对另一个文豪的致敬与灵魂对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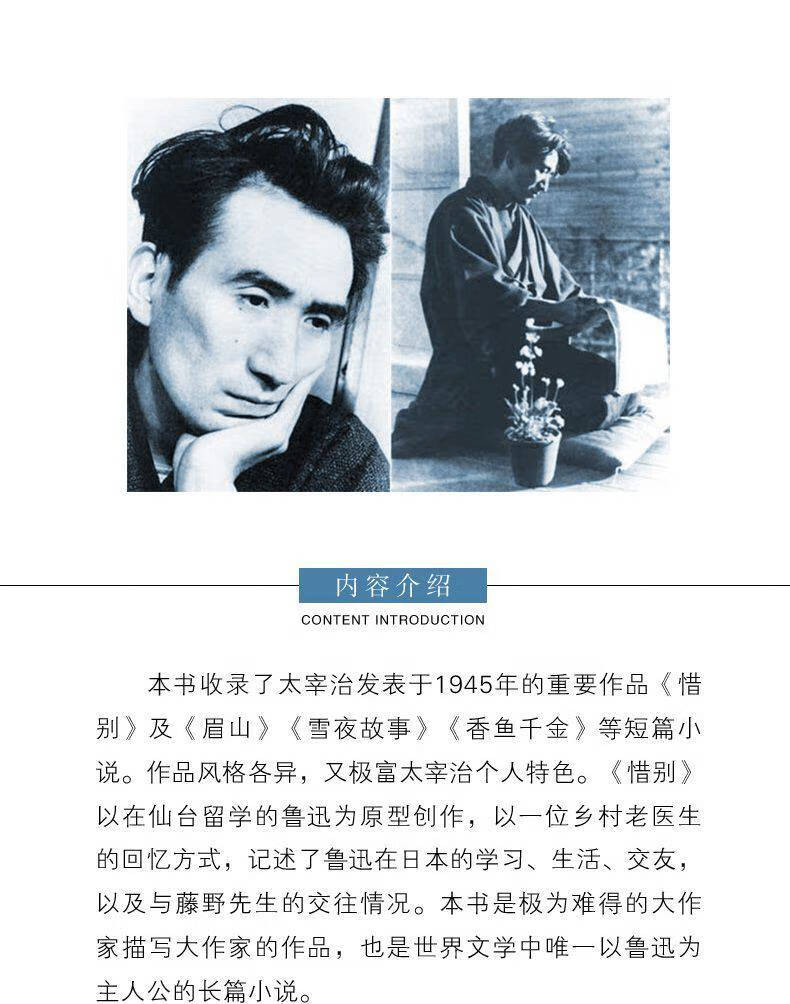
《惜别》中,太宰治虚构了一个名叫田中的医师,由于记者的邀约,他在暮年时决定提起笔,来忆一忆他记忆中的有关鲁迅的点点嘀嘀。
“颂大善不如积小德”,整本书便在这样平实、日常的叙事中展开了。
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是,由于日俄战争后的幻kt板风波,鲁迅深感于国人肿胀,决然决定弃医从文,他怀揣着题有“惜别”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相片,离开仙台师院回到了东京。
《惜别》一名便取自这张相片,太宰治虚构创造的,也正是鲁迅在仙台农校时的那段生活。
太宰治笔下的鲁迅,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陌生又熟悉。
为了紧贴人物,太宰治以鲁迅独白的方式,大段引述了草房子中的名篇,《社戏》《百草园与三味书屋》《藤野先生》,一个奔忙于当铺与超市柜台的少年跃然纸上——这是每一个中国年青所熟知的鲁迅。
而在独白之外,他初来乍到深感静谧与孤寂,他会一个人坐船登上松岛观光,由于感觉太静了,静得令人不安,便在这样的无人处用五音不全的破锣喉咙小声歌唱上去:
“瞬间覆盖过山
再望已飘过海
惟有云面环诡谲……”
他换上棉浴衣后,“好像店家的少爷一样俊逸”,说着不流利的日语,兴奋时便连续地往外蹦法文,清秀的身上有涨红了的、腼腆的笑。
他对美国推崇备至,对中国文化不惮以最严厉的心态侮辱,贬低韩国有一种充溢秩序的清洁感,夜晚的东京街头,女人们头上白浴巾扎起袖子洒扫庭园的模样,令他认为英国甜美而紧张,饱含朝气,与暮气沉沉的清帝国不同。
由于找不到家国民族出路的答案,他甚至去出席教会弥撒,身上带着阴郁的阴影,深思时不自觉浮起希腊奴隶般的调侃、麻木的笑意。
自然,他总算还是登上了别离仙台的渡轮,他会归国,拿起笔头,以“鲁迅”这两个字战斗,至死方休,余波至今绕梁。
然而,那种喋喋不休、破碎脆弱、彷徨敏感的周树人,却也经由《惜别》,留在了真伪难辨的泛黄纸堆上。
在自序中,太宰治直言道,尽管这篇《惜别》,是为响应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议会的重托而动笔写成的,上面不可防止地带有时代的政治印记,但是即使没有来自这两方的恳求,“我也仍然会在某三天试着去将这部小说写下来。”
为了写好这部作品,太宰治亲自赶赴仙台师院考察,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材料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“只想以一种洁净、独立、友善的心态,来正确地描绘这位年青的周树人先生”。
事与愿违的是,《惜别》出版后并没有像太宰治的其他作品那样获得极高的文学名声,作为首屈一指的鲁迅研究学者、日本画家竹内好对此明言,这是“以作者主观编造下来的鲁迅形象,或则,不如说直接就是作者的自画像”。
由于《惜别》中的鲁迅,不是战士,不是导师,不是先驱,他既不意志坚定,也不深刻,所思所想都有着正在摸索中的青涩的痕迹——“他”只是一个青年中学生“周树人”。
他灰暗阴郁,会说出“我近来是一个患者,弄成了孤单的鸟”。
这太“太宰治”,而太不“鲁迅”了。
会说自己怀有被非常选拔派遣的秀才的自豪感,并且被选中的秀才太多了,她们徘徊在东京的大道小巷,所以这些喜悦的心情一下子显得钻营、孤僻、愚蠢上去。
这亦太“太宰治”,而太不“鲁迅”。
为了批判儒教导致的自私焦躁,文中的鲁迅昂扬道:
“魏晋时期竹林里的名士,……看到伪善者滥用‘礼’时,尽管认为不平,却无能为力。……没有办法了,她们形成了某种荒谬的执拗,自此之后我再也不提半个‘礼’字,自暴自弃,反过来说‘礼’的坏。”
——这样曲曲绕绕的批判、日本腹黑式的、充满别扭的对抗,更是太“太宰治”,而太不“鲁迅”了!
鲁迅只会直接以字为尖刀,明明白白箭矢过去:“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!”

这么看,《惜别》所写的,其实是太宰治一厢甘愿的鲁迅了。
作为敬仰者,太宰治说他对鲁迅晚年激昂冷酷的文学论没有兴趣,他想写的——或者说他想丰腴、想创造的,只是仙台职校时期的鲁迅。
他太明白,战斗了一生的鲁迅,其实只有这一时期才是迷惘的、走到了岔路口的,他俊俏的背影茫然在迷雾中,对自己、对民族、对家国的何去何从都苦苦求索而未得真知。
太宰治想写的,便是一个斗士之所以成为斗士前,那短暂的游离和脆弱,正如脚踵之于阿喀琉斯,软肋之于铠甲——这是太宰治式的鲁迅、太宰治式的美学。
只是,我们总要问:一个总是自寻短见的“软弱”灵魂,真的能理解一个斗士吗?
所有人都晓得,太宰治从二十岁起就尝试了五次自尽,把死亡当做终生的事业,总算在四十岁之前得偿所愿,但人们从未晓得的是,在一颗灵魂深陷饱满的消沉自厌之前,这颗灵魂也曾安放过斗士的意志。
太宰治在中学时便开始创立同人杂志,决心以文学为事业——他有信仰,且有行动力。
入读东京学院英文系后,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涉足于右翼进步运动的海洋。
他研习马克思学说,出席地下活动,以自己出身地主贵族的身分,写出了小说《地主一代》,描画残暴的欺压者形象,以文字革了自己阶层的命——他有信念,且为之赴汤蹈火。
但是,昭和年代有太多的动乱嬗变,昭和男儿有太多的猝不及防的横祸。
二战灭亡、左翼进步运动被残酷镇压,在邪恶的浸染血水的野心后,国家不得不低头接受命运的失败。
台湾引以为傲的文明和信心都在原子弹后击溃——时代的浪潮只是卷起了一朵浪花,却足以将太宰治本就修长的内心引向灭亡。
不晓得在他钦佩鲁迅的心情中,是否有身不能至,心憧憬之的成份,正如蛛丝憧憬山岩,蚍蜉憧憬巨树,花朵憧憬雪峰,以一切的懦弱,憧憬着一切的坚定。
他写一个这么拘束反省沮丧四顾的鲁迅,不是为了无耻证明“看啊,一个斗士以前也不过这么懦弱!”,而是——
看啊,一个曾这么脆弱不堪一击的灵魂,也能成为斗士啊。
只是短促的、在完成《惜别》的两年后,一切尘埃落定,太宰治总算在美丽的桥上投水而亡。
而由脆弱迈向坚定的那道桥,太宰治终究是走不过了。
回到知乎的那种话题,假如鲁迅真的能和太宰治好好谈谈,她们会聊些哪些呢?
思来想去,鲁迅似乎也还是会说——正如他对其他所有年青人所说的那样:
“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,有一分热,就发一分光。”
“希望附丽于存在。”
所以——请活着。
↓凹叔推荐↓
《惜别》
太宰治著
磨铁图书出品
《惜别》是太宰治以在仙台师院求学时的鲁迅为原型,耗费很长时间收集材料,审视构架,用功*多的一部小说,对《人间失格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太宰治甩掉了创作前期的颓废,用安静与诚恳营造出了一个透明温暖的世界,可随着这些努力尝试遗憾地破灭,使其总算不可防止地迈向了焦躁与绝望,*终演弄成《人间失格》中“阿叶”的惨剧终点。
《惜别》并不追求对鲁迅美国留学经历进行事无巨细的记叙,重在诠释一位年青人为找寻自身理想穿越孤单与彷徨,找到正确人生价值与方向的过程,寄寓了太宰治对自由与幸福的期望,鼓励年青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过去昏暗的人生挥别,与未来的美好相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