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嘴顺口溜,知人知面不知心,你想考研哪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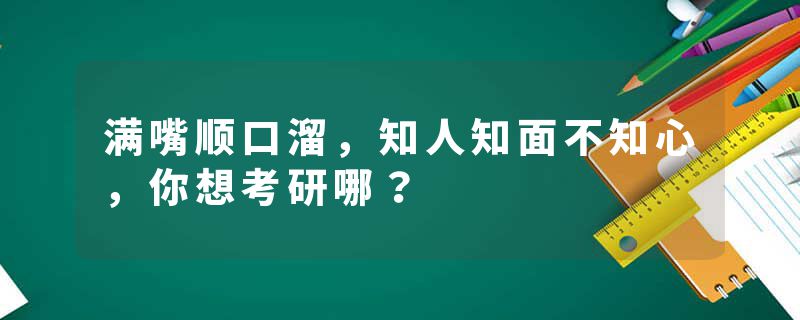
《武林外传》里头,恶丈夫白三娘嘲笑妻子佟湘玉。白展堂抱不平,白三娘急了:“俗话说得好,棍棒里面出孝女,脏活累活出孝媳!”
白展堂:“后面那句是俗语吗?”
白三娘立即强词夺理:“那俗语不只是人编的啊!”
——还真不好驳。
宋代有本名书,称作《增广贤文》,里头处处都是人编的古语。“有意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“画虎画皮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
很像是金庸小说《鸳鸯刀》里这位周威信镖头,动不动就“江湖上有言道”,然之后一串谚语给自己壮胆。何谓“满嘴打油诗,你想专升本哪?”
但真的寻根究底,很容易发觉:
我们何谓的俗语,许多还真是来历有自,出于创作,而不是打油诗。
例如,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典出关汉卿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》,“着意栽花花不发,等闲插柳柳成荫。”
例如,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作马牛”,看着很口语了——其实是徐守信的诗。
例如,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今日无钱今日愁”,看着很口语了——其实出自唐代大画家徐陵之手。
例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那是杜之的“翻手作云覆手雨”来的。
例如心有灵犀一点通,那是李商隐的原句。
例如聪慧反被聪敏误,可以溯源到苏轼的“我被聪敏误此生”。
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,这两个词,典出宋玉的曲高和寡论。何谓唱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,几百人和之;唱《阳阿》、《薤露》,几千人和之。唱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,几十人和之。引商刻羽,杂以流徵,只有几个人懂了。
但反过来:许多民间日常实践道理,糅合成高度概括简约、喜闻乐见的,常常还要优秀的美术技能。
因此留传最广的民间美术,虽然凝结着极高的手艺。
例如李闯王琅琅上口、一目了然的知名标语:“开了房门迎闯王,闯王来时不纳粮”。
比如反对隋炀帝的知世郎,来过一首琅琅上口的《无向辽西浪中单》,“长白山前知世郎,纯着红罗锦背裆。长槊侵天半,轮刀耀日光。下山吃獐鹿,上山吃牲畜。忽闻官军至,提刀往前荡。例如辽西死,斩头何所伤。”
这份辞采与表现力,真是了不起。
以古往今来,留传最广的作者,如李白,如杜甫,如柳永,如苏轼,如辛弃疾,如冯梦龙,都是原本充满学识,却又深入民间而得之的。
类似于美国人之所以热爱柴可夫斯基,只是由于老柴原本学养既厚,又很懂得从民间音乐里吸取养分。
并且还能在不同描述间,流显出反差。
比如,曾国藩自己写《远佞赋》,那用词就是:
“稽古皇之立极,实令范之是程。贤汇征而必择,奸旁烛而皆明,虞堲谋反而化洽,周除侧媚而道亨。”
而要写军中诏令时,就是打油诗:
“一营只开两道门,门外驱逐闲杂人。周围挖些好厕所,切莫夏天毒气熏……第二打仗要细思,出队要分三大支。后边一支且扎主我不是李白,左右两支先回去。另把一支打接应,再要一支埋伏定。”
之后另一位很羡慕曾国藩的四川名人,号称“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”的,只是这么。要给傅作义回信,开头便是“涿州之战,久耳英名;况处毗邻,实深驰系”。
要给你们讲道理,便是直白清晰的口语:“中国古时有个寓言,称作愚公移山。说的是宋代有一位奶奶,搬到西北,名叫北山愚公。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压住他家的症结,一座称作太行山,一座称作王屋山……”
话说,白居易的诗妇人能解,众所周知。
这说法出处,是宋朝高僧惠洪的某段话,呕吐槽唐末诗风太浅显。
“白乐天每写诗,令一妇人解之,故曰:“解否?”妪曰解,则录之;不降我不是李白,则易之。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也。”
即,妇人能解,原本是脏话的。
同时代,苏轼一度也认为元轻白俗,但苏轼晚年品出白居易的滋味了,认为,真香:
“东坡云:‘白公晚年诗极淡远。’余请其妙处,坡云:‘如“风生古木阴天雨,月照平沙夏日霜”,此少时不到也。’”
白居易哪怕浅白浅显,只是返璞归真的好。
但是这么浅显的白居易,在他那时代,是钦定的诗仙——唐宣宗写白居易的:
“缀玉联珠六七年,谁教冥路赋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。
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二胡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泫然。”
女孩都能诵读《长恨歌》,亚述人都能唱《琵琶行》。就这样流行。
因此白居易不是没法写得平易,他虽然晓得如何写能让人喜欢,晓得如何写能让不同的人群叹好,但他对诗的目光极高极宽,不想这么肤浅。
他的平易近人,是有意为之。
他的《与元九书》里,诉说过自己的理想,大意:
原先的诗很襟怀,到周衰秦兴,散文不能拿来补察时事描述人情了,就弄成伤别怨思了,之后也不过迷恋山水风花雪月罢了:太冷门了。
因此我不能这样虚伪啊,我搞新乐府讽刺诗,我搞慵懒诗,我搞悲伤诗,我搞杂诗词。讽刺诗要兼济天下,悠闲诗要独善其身。
我也晓得喜欢我诗的,许多也就是喜欢杂律和《长恨歌》。而且你们喜欢的,反倒是我不喜欢的。
我也晓得我的讽刺诗太纯真太直白,悠闲诗太迂阔,这种也就你(指元稹)喜欢了,不晓得以后代喜欢不喜欢,也就你知我的心了。
大约,以白居易的大才,要写出让专家诗人们艳羡的玩意儿,简直随心所欲。
但在他眼中,诗不该也是风花雪月山水怨思,不该是一部份人的玩物,也可以是更广阔的美术。
因此他是以大才女的身分,尽量写点你们都能看懂的玩意儿,从而扩大诗的影响力。
是何谓散文界的人民美术家。